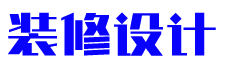装修问答
母爱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发布时间:2025-02-06 20:48:24
在八十岁时我母亲有她的最后摔了一跤,之后,她的脑海里徘徊自由穿越时间。有些日子,她到婚礼和所发生半个世纪前的葬礼。对别人,她主持的家庭晚餐煮熟周日下午为孩子谁是现在灰色的年龄。通过这一切,她躺在床上,但跨越时间移动,死几十年来与速度之间的旅行和缓解超越物理科学的恩赐。“哪里的罗素”她问有一天,当我来到在养老院参观。“我米罗素,“我说,她凝视着这不大可能杂草丛生的身影走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未来,并及时驳回。“罗素的只有这么大,”她说,握着她的手,掌心向下,从楼的两个脚。那一天,她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的妻子在后院的苹果园后面朦胧的蓝色弗吉尼亚山脉的景色,而我是一个陌生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一天清晨,她打电话给我在纽约。“你来参加我的葬礼今天?” 她问,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与被唤醒。“你在说什么,在上帝的份?” 是最好的答复,我可以驾驭。“我今天被埋没,”她轻快地宣布,仿佛宣布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件。“我会给你打电话回来,”我说,挂了,当我做手机的背面她是对的,虽然她不是没事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她是不是。她一直是一个小女人-轻薄短小去骨,结构精巧-但是现在,白医院被单下,她变得微小。我有巨大的,凶狠的目光想到了一个娃娃。这里一直是一个凶猛的她。这表明在下巴那愤怒的具有挑战性的推力时,她发出的意见,和一个伟大的,她一直签发意见。“我告诉人们什么是对我的脑海里,”她一直喜欢吹嘘,“他们是否喜欢还是不喜欢。“ “ 这并不总是好的政策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你的头脑,”我曾经提醒她。“如果他们不喜欢它,这太糟糕了,”是她的习惯回答说,“因为这是这样的我。“ 于是,她,一个强大的女人,决心说出自己的头脑,确定有她的办法,决心弯曲那些谁反对她。她投掷自己在生活,使她似乎总是在奔跑的能量。她跑了鸡后,斧头在她的手,在斩首,将晚餐摆在锅里决定。她跑了,当她做床,跑到她的表中设置。一个感恩节,她烧得很厉害时,从地窖里跑起来甚至与礼仪火鸡,她绊倒在楼梯上跌落下来,在内脏,肉汁炎热的碎片底部结束,并殴打火鸡。生活是战斗,胜利是不是懒惰,胆小,药店牛仔,玉米粥,嘴不敢告诉别人什么是在他的脑海。她跑了,但现在运行结束。一时间我不能接受不可避免的。当我坐在她的床上,我的冲动是争论她回到现实。在我第一次访问在巴尔的摩医院,她问我是谁。“拉塞尔,”我说。“罗素的出路西部,”她劝我。“不,我就在这里。” “ 猜猜我从哪里来今天?“ 是她的回应。“在哪儿?” “ 一切从新泽西的方式”。 “ 号你已经在医院住了三天,”我坚持着。所以它去,直到一个医生走过来给那些口头测验之一医疗应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完全失败,给错误的答案或根本没有。然后一个惊喜。“你什么时候过生日?” 他问。“1897年11月5日,”她说。正确。绝对正确的。“你怎么还记得吗?” 医生问。“因为我出生在盖伊·福克斯日”。 “ 盖伊·福克斯?” 问医生,“谁是盖伊·福克斯?” 她答道,韵我听说过她多年来背诵一次又一次:“请记住十一月第五,火药阴谋和叛乱我看没有理由火药叛国罪应该永远不会忘记。“ 然后,她怒视着这个年轻的医生,所以不了解情况Guy Fawkes的'计划失败的打击国王詹姆斯了他的王位与火药桶在1605年。“你可能知道很多关于药,但你显然不知道任何的历史,”她说。经告诉他正是在她的心中,她再次离开了我们。然后医生诊断无望的衰老或血管硬化。我认为这是比这更复杂。十年或以上,这是她曾经生活的攻击凶猛已经转向一个怒斥无力,无聊和缺乏爱心,太多的时代已经带来了她。现在,最后重重地摔了一跤后,她似乎已经打破链,囚禁她的生活,她已经到了仇恨和返回通过谁爱她,在她需要的是一个时代的人居住的时间。渐渐地我明白了。三年前我已经从纽约下来到巴尔的摩,她住的地方,为我的不频繁互访之一,后来,写了她的一些陈腐的意见去寻找一线希望,指望她的祝福,而不是的负担别人与她的苦难。我想它真正为是,如果她不是更开朗期间我访问我不会来见她经常构成威胁。儿子有能力这样的信。这一次是写在父母的永恒力量,一个天真地认为年龄和磨损可以通过意志努力来克服,所有她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动员讲话充一次萎靡不振的精神幼稚信念。她回信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愉快静脉意在展示,我想,她是她的修补方法。参考我的访问,她写道:“如果我似乎不高兴你的时候,我是,但没什么好说的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因为我只是太很疲惫和孤独,我只是去睡觉,算了吧。“ 她是那么七八。三年后,最后重重地摔了一跤后,她已经成功地忘记了疲劳和寂寞,并夺回幸福。我很快就停止试图辩称她回到了我认为是真实的世界,并试图去旅行以及她对那些梦幻般的旅行到过去。当我到达她的床边有一天,她容光焕发。“今天感觉不错,”我说,“为什么我不应该感觉很好吗?” 她问。“爸爸的今天要带我到巴尔的摩上了船。” 在那一刻,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站在一个码头,在切萨皮克湾蒸笼与她的父亲,谁已经死61年等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在白宫,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并在晶阳光光束面前的未来延伸。“上帝的绿色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她的父亲也许会说,如果我已经能够踏进我母亲的时间机器。关于她的父亲,我的祖父,我妈妈的童年和她的人,我知道的很少。的世界曾经生活和死亡,虽然这是我的血液和骨骼的一部分,我知道一点关于它比我所知道的法老的世界。这是没用的现在,要求从我母亲的帮助。她的头脑轨道很少触及目前的审讯超过了片刻。坐在她的床边,永远与她联系,我想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和一般的孩子,以及有关防止他们的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断开从相知。孩子很少想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之前,当时 代终于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就没有父母留下来告诉他们。如果家长确实提起帷幕了一下,它往往只是击晕年轻用更难的生命是如何在旧时代。一些示例性的故事我已经犯了这个时候,我的孩子在20世纪60年代初,生活是小富裕的生活。这激怒了我,他们的童年是应该的,因为我想,这么容易当我自己曾经去过,因为我以为,这么辛苦。我已经开发了讲课他们生活的残酷在我一天的习惯。“在我所有的日子,我们得到的晚餐是通心粉和奶酪,而我们很高兴能得到它。” “ 在我的日子,我们没有任何电视。“ “ 在我的天......” “ 在我的天......” 在吃饭一天晚上儿子得罪了我一个报告卡不够用,因为我清了清嗓子演讲,他凝视着我,用一个表达式难言的辞职所说,“告诉我它是如何在你的一天,爸爸。” 我很生气,因为他说,但我自己的愤怒已经成为那些古老的孔,其过去的高选择性记忆变得透明不诚实的一个甚至以小的孩子。我试图打破这个习惯,但一定失败。我们之间有一个关于时间的争议。他看着在那一直是我的未来在一个令人不安的方式的时候。我的未来是他的过去,并且是如此年轻,他却无动于衷过去。当我徘徊在我母亲的床上听着从她小时候的一些信号,我意识到这同一争议我和她之间已经存在。当她年轻的时候,与她之前的生活,我一直是她的未来,怨恨它。本能地,我想挣脱,并不再是由她的时间定义的生物。好吧,我终于做了,然后用我自己的孩子我见过我的令人兴奋的未来成为他们无聊的过去。结束的线,这些无望与我的母亲参观使我希望我没有揭去我自己过去那么不小心。我们都来自过去,和孩子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走进他们的决策,要知道,生活是人类的时间长了向上伸展编织线,它不能由一个单一的跨度定义从尿布旅程导流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