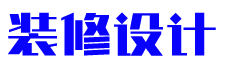装修问答
为什么棕榈树不分杈
发布时间:2025-02-08 19:04:22
高原多棕榈。深山野岭,溪涧河谷,房前屋后,田边地角,到处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在我对棕榈的最初印象中,竟弄不清它到底像个英武汉子呢,还是像个柔弱少女。在西双版纳,葫芦岛上美丽的纺锤棕我见过,允景洪街上风姿绰约的油棕树我也见过。那亭亭玉立的身姿,美伦美奂的韵味,总让人想起在田畴间结队而行的傣家少女。而另一些时候,在酷热难耐的峡谷,陡峭难行的山崖,偶尔挺立的一株棕榈,又让人俨然想起那些伟岸的战士。然而,见过也就见过,于南方这种常见的树,除了知道棕榈壳可做绳缆之外,却一直没什么了解。没想,我会与一株普普通通却又精灵古怪的棕榈相识相知———就在我的窗外,在咫尺之间。那是一株极普通的棕榈,是好几年前一个朋友送的,初为盆栽,高不盈尺,茎若拇指,七、八扇瘦瘦的叶片,由一茎同样细瘦的叶柄支撑着,极力地、平平地向外伸展开去,看上去虽颇有些动人,却柔弱得叫人担忧。后来搬家,不小心把那个花盆打破了,幸好住在一楼,外面墙角有块空地,就顺手把那株小棕榈移栽到了地里。那是楼房与楼房间的一小片空地,简直就是个死角,宽不过两米,三面高墙,难见阳光,原本是个极不适合花木生长的地方;不久,同时栽下的几株草花都相继枯黄凋萎,惟独那棵棕榈,不但没死,反倒慢慢长大了;树干直立着,不分杈,不歪斜,举着十多片叶子,像十多个为了欢呼而扬起的阔大的绿色手掌,慢慢就高出了我的窗户,很快又窜过了矮矮的围墙,直向云天伸去。不过我还是没拿它当回事,也从没给过它什么关照。相反,我倒伤害过它:家里有几回插花,曾砍下过几片棕榈叶,剪成蒲扇一样大,衬上鲜花,倒也好看。真让我注意到它的是那个雨季。那年雨水多,有时下得天昏地暗,屋里潮得发出阵阵霉味儿,弄得心情沮丧,似乎人心都要生毛,原本该做的事却做不下去。那天呆在家里百无聊赖,免不得感叹生命的流逝是如此的无情。却突然听见窗外的棕榈树叶哗啦啦地响。细看,外面风并不大,它怎么了过了一会儿,一阵小雨洒下来,它竟发出千军万马般的声音。我忽然觉得它长大了,有了灵性,就像一个人,变得极敏锐、极敏感,一点响动,都会引来它的一片喧响。以至它常给我造成错觉———明明是不大的一点雨,经过它的渲染放大,就成了一片吓人的风雨。好几次夜半被它吵醒,以为第二天必定出不了门了。早起一看,地是湿了,却绝无泥泞。云南高原上的少数民族是信奉万物有灵的,以为什么都是神灵的物化,比如山、石、水,甚至一棵树。我于是怀疑那株在阴湿的墙角呆得太久的棕榈树活不了几天了……可一个雨季下来,窗外那株棕榈竟长高了一大截,一副成熟汉子的模样。且那样地富于灵性,对周遭世界有着那样强烈的反应,这就委实有些古怪了———或许,它在夜里的喧哗,是要告诉我什么而它在小雨中发出的呐喊,正是某种警告和劝喻甚至,它是要我注意到它的存在,渴望与我作一次简短的交谈我突然有些惭愧———灵性枯萎,性情浮躁,对生命、心灵视而不见,不正是现代人最容易染上的疾病么回想起来,我什么也没给过它,没为它除过草,也没为它浇过水,遑论关注它的心灵四面都是墙,它只有一点极为可怜的生存空间,它必须拼命地踮起脚来,去接受从墙缝中漏进来的极少一点阳光和雨水。生命须自强。每当风雨大作,它便挺直腰杆,与之搏斗,而在月明风清的夜晚,它也会发出轻柔的吟唱。那便是我所谓的错觉,它的精灵古怪。那也真是错觉,错在我并不懂得它的艰难、坚韧、坚强和灵性,不懂得即便一株无言的棕榈,也有它对自己内心的表述。我索性把写字间跟卧室调换了一下,那样,我抬头就能看到那株棕榈了。某天,朋友来家小坐,我把他让进我小小的写字间,说:“见了吧,多寒酸”他没吭声。闲聊中我说起了窗外那株精灵古怪的棕榈,朋友注视窗外那株棕榈良久,突然感慨道:“你错了,你够富的了,居然能有一棵这样的棕榈”我朝窗外望去,见那挺直的树干,阔大的叶片,风格简洁,傲然不群。跟几年前相比,它的叶子已不是几片,而是几十片了———谁能说得清,它到底会长到多高多大,会给多少人送去它的祝福或警示呢